在我動手寫出投票背後理由的時候,朋友傳來訊息:「Elliot剪頭髮和做割乳手術了。」新聞稿連結中,他登上《TIME》雜誌的封面上,印著一句話:I’m fully who I am。「我自由了。」
想起直到幾年前,我也才終於完全是我了。
那時不由自主地,寫下這個句子。
如今,我盯著它,又忍不住重新思考,自由是什麼?
如果不用再跨越,是否意味我在我的世界裡,已沒有任何阻礙?
「若人類是透過語言的濾鏡來觀看這個世界,那麼未知的詞語是否就意味著對世界眼光的死角?……藉由認識這些詞彙,我將這些東西召喚到了自己的認知世界裡,或者說,我在自己的世界裡創造出了這些東西。」──李琴峰《倒數五秒月牙》〈聖夜絲〉
如果生命是創造,創造會導致無垠的混沌中的一道邊界,於是,再努力跨越它。那麼,自由也許意味著,從此處開始,不再創造限制和邊界,於是我也沒有了需要跨越的目標:我的女同志生命成了一灘死水。
那麼,真正的問題是,我為什麼不再「跨越」?
曾經,我的慾望是所向無敵的,我拉開一段自認無人探索的範圍,更有一段時間,我總是在想所有的「我們」,以為走每一步,都是為了所有人而跨出。
跨越的前與後,因為一道界線存在,前面的路必須在自己踏出去的時候,一步步拓展疆界。也因此,感覺到跨越,那些「里程碑」的時刻,我個人曾經意識到「跨越」的掙扎,都因為前方完全的空無,有「毀滅的預感」和義無反顧;而已成功跨越的,則無可避免成為被我留下來的「後方」。我親手設定了我的必經之路,然後再一步一步地向後拋擲。以至於,如今再閱讀人們描述跨越,我感覺到自己是個,將所有歡迎光臨的途徑親自銷毀,一位「過河拆橋」,意圖抵達無人能及的彼岸,「自由的女同志」。
但是,哪有「必經之路」呢?如果有,豈不是成了一種詛咒呢?
能夠成為濡沫建站早期的駐站作家之一,獲得完整跟大家分享心得的資格,很感激。看似沒有其他具體行動,我卻是因為這個資格,才能一直將書寫工作放在心上。也是剛好在提筆不久的2021年3月,「他們在島嶼寫作」系列,一部由導演朱賢哲拍攝七等生為主角的紀錄片《削瘦的靈魂》,才在高雄放映。朋友們紛紛去看電影,還帶回一本漫畫家曾耀慶為七等生繪製的短篇〈跳遠選手退休了〉給我,裡面引述一句小說原文:「沒了責任的意志,自由是一種虛無」。
這次我的票投給了正好也是最終入選的三篇〈普通故事〉、〈工寮課:浪犬〉、〈新年出走〉。但我預計像收到遠方來信那樣,以信件往返的設定,用系列文字回應有獲得泡友投票的每一篇徵文。入選與不選的說明,都會融合在回應篇目中的文字裡。如果疲於閱讀那麼長的系列,可以止步前言──我的選稿考慮是,來稿明確記述「異質邊界的描述」、「跨的準備」、「越的狀態」三階段供指認,不同的階段和倒數的方法──其他都是溢出的交流而已。
在我看來,不同徵文主題,都會開啟對話。所以我非常期待透過大家有意識的書寫,喚起自己的意志,以及那些已經被跨越,留在人們身後的事。我的跨越是我的詛咒,如果可以,如果可以,我想試著「跨越」詛咒,抵達祝福的邊界:如果妳準備好了,說不定能輕推妳一把;如果妳發現我在妳的後方,那就,換妳當鬼。
我為自己文字經營的更新遲緩向各位表示歉意,尤其說明來的那麼遲,還要分批陸續釋出。作為載體,我身上攜帶的是同婚時代之前的程式碼,現在輸入指令,仍可以產生膝反應式的回饋,但是意義不大。還需要更多時間,才能完成程式碼的全面更新。在仍偏執的修訂、編寫程式碼的時候,陸續寫下這些與其說是評語,不如說是由「跨越」這個主題觸發對話的一連串過程,請收下我從開始讀到這些,決心要嘗試再檢視個人邊界的思考和回應。讓文字勾引文字,用情感回應情感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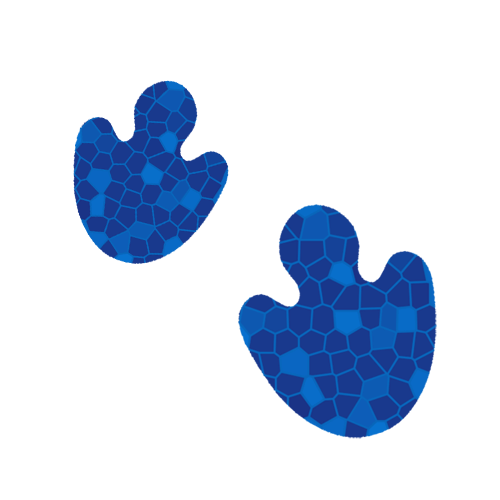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留言
You must be logged in to post a comment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