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西安那頓晚飯後,我跟Han幾乎每天都一起用晚餐,有時跟幾個投契的學生一起去回民街吃羊肉串和肉夾饃,有時只有我們倆去附近的西餐廳吃些中式西餐。朝夕相見,我認識到她別於工作的一面,那是她的社會運動——同志平權。她讀文化研究,興趣是意識形態、階級與性別研究,畢業後雖然做一份與興趣並不相符的工作,可是公餘時間就是她發揮所長的地方,她是同志組織的核心成員,那機構主要做政策倡議、教育大眾和為小眾充權,她在那裡做義工已經五年,由一個實習生開始,到現在已是籌委成員,負責培訓義工,統籌大小活動。
每當她說著她的熱情時,眼裡總閃著光,她吸引,是一種因著自身熱情而來的吸引,我被她打動,於是答應回港後跟她去一個電影放映會,看個究竟。
那場地隱藏在工廠大廈之內,Han把我介紹給放映會的搞手阿木,她是同志組織的核心成員,作中性打扮、一頭蓬鬆短髮,中等身形,眼睛圓圓,聲線響亮如鐘,一開聲就充滿魅力。
「聽Han說,你讀性別研究的啊!」阿木說,眼裡閃著光。
「對啊,兩年前畢業,都是些理論,不中用,哈哈。」
「是未見用途而已啦,我們在找人寫東西,有興趣嗎?」
「寫什麼類型的?」我感興趣地問。
「都可以,只要是從性別角度的就可以了。」
我想起自己跟丁丁分手後看過的一堆文藝片。
「好,我可以。」
我們交換了聯絡方法,跟其他人聯誼一下,互相介紹,說說電影,當天就交了好幾個新朋友。
我跟Han一起離去,在去地鐵站的路上,我謝謝她把我帶來這裡。
「人要活在社群內才不會感到孤獨。」
這番話的意思很直接,但我想到的是她的孤獨,女友不在身邊,只能把熱情投放到更大的社群上。
「我不是說我孤獨,而是我作為同志,我覺得參與平權近乎是義務,但這只是我對自己的要求。」
「你的確對自己要求很高呢。」
「沒要求的話是不會進步的,個人如是,社會如是。」
我在她面前總像個小妹妹,讓她分享她的見聞,然後受住她的影響,去做些超乎自己想像的事。
同時,電影會的同志使我深刻,他們都是同志,卻不是我在派對中看到的那些想要變成別人的人,而是一個個個體,他們雖然不一定自信滿滿,但卻勇於擁抱自己的身份,或嘗試了解自身的一群。我們之間的對話雖然短暫,但卻並非流於表面的無聊問候,她們關心我所關心的,反而我像個空洞的人,只會理論,我讀的性別研究到底改變了我什麼?我把我的所長放哪裡去呢?如果沒有學以致用,那我所得到過的啟蒙和掙扎又有什麼意義?
是熱情,唯有熱情。
我的熱情在哪?我的時間都放在哪裡了?就是一段又一段無結果又無意義的關係。跟他們的交往,最後只剩下迷惘,我的廿來歲都花在追追逐逐的無謂關係上,那些算不上是愛情的關係,雖不能說毫無意義,可是所花費去處理的力氣之大,令人懷疑是否值得開展。
回家後我坐在電腦前,想想我的第一篇文章,於是以我最喜歡,艾慕杜華的《慾望之規條》來開始,寫那個為愛瘋狂的安東尼奧,展現在愛與慾望面前,眾生平等;面對愛人,我們也只能按著慾望的規條而行。
文章出來之後阿木很滿意,文章的點擊率雖然沒有很高,但卻為組織添了新氣象,他們很需要我這種可以從性別角度切入的作者,寫一些文藝類的文章,我不但高興,而更重要是有種使命式的滿足感被滿足到,我說可以繼續寫,我看過的同志電影可多呢!
之後我按住每星期三篇短影評的速度發表文章,Steph消失了,程永也沒有找我,我空出了很多時間,像剛剛跟丁丁分手後多出來的空餘時間,今次卻不再找人來填補。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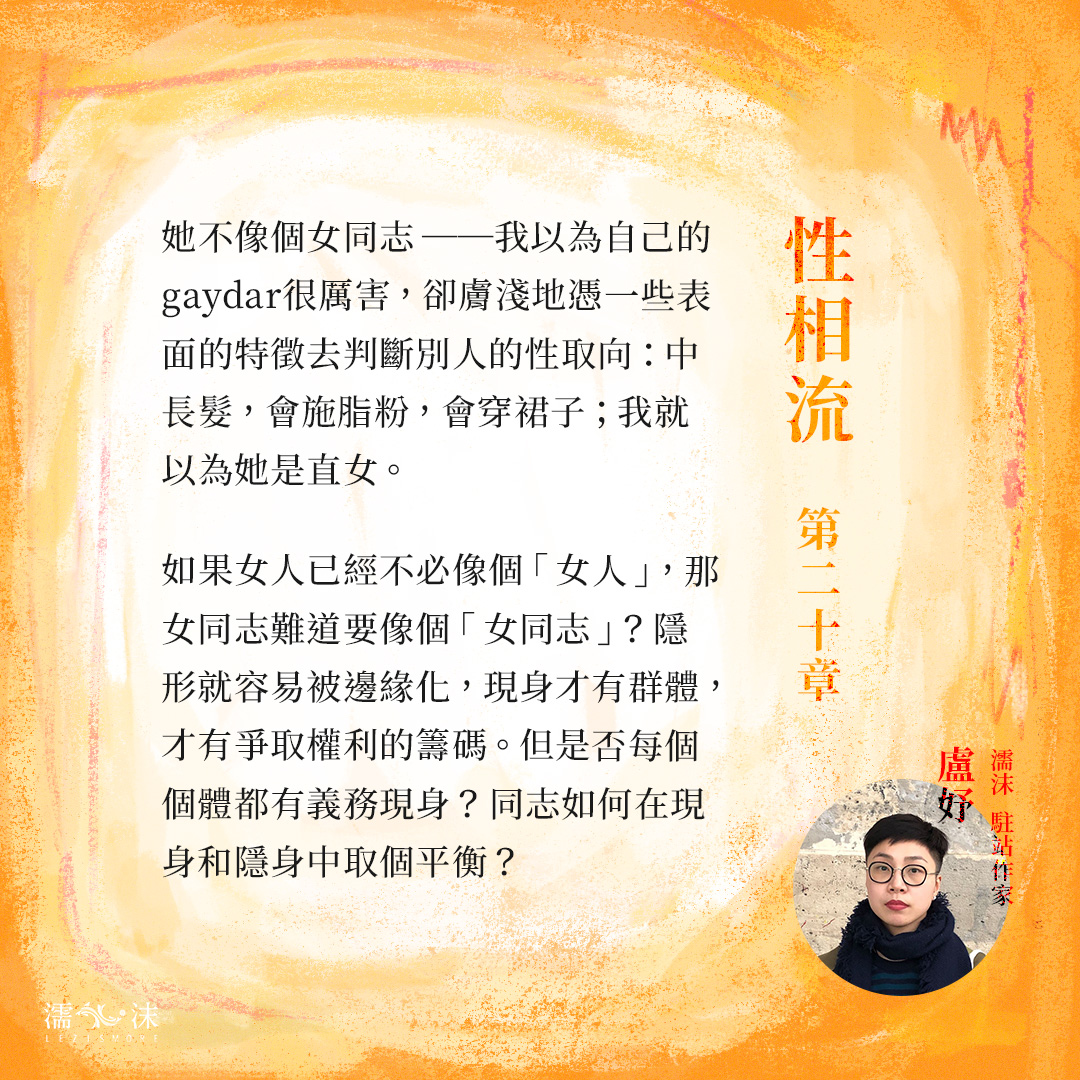

留言
You must be logged in to post a comment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