命名,作為魂魄的根
如骨肉相連般,姓名仍然是辨識自我身份時的重要存在。
Echo與濡沫團隊聊起自己的變裝國王姓名:「這名字的發想過程其實滿瞎的,但我一開始想超久,想說要叫麒麟,還是叫哪吒?但是我後來不想要花太多時間去想名字,最後就決定是哪吒(Naza)──蓮花化身的那個哪吒。」她一口氣說完。Echo的敘述方式總是這樣:雲淡風輕的口氣、簡單到近乎讓人詫異的理由,看似隨性無緒,但自有一套內在邏輯。
哪吒是道教故事裡的叛逆「魔童」,也是台灣民間信仰裡蹦跳萌樣的三太子。之所以選擇這哪吒(Naza)這個名字的理由,也讓人會心一笑:「我一開始選哪吒,是因為他有風火輪,我想說我也會溜冰,有機會可以穿花式溜冰鞋表演之類的。第一個關聯其實真的是溜冰鞋,很瞎。」
哪吒的故事對歐美人來說普遍陌生,在通俗小說與神話裡,哪吒鬧海犯事;為了不牽累父母,他剔骨還肉,心一橫擺脫了肉身與血緣,死了凡胎,魂魄重新在一具蓮花化成的軀殼裡活下來,還獲得煞是威風的扮相,腳踏兩枚風火輪,手持金尖槍,形象十分鮮烈。
「哪吒他也算是離開了父母吧,跟我留在荷蘭的原因有點像,不想離家人太近。加上台灣人的身分對我來說是重要的。」她說。

哪吒、大聲公、Tiffany綠溜冰鞋(找亮點)
圖片授權:@dragboinaza
而哪吒(Naza)的寓意,也讓我們聯想到宗教色彩。
當濡沫團隊問及Echo自身的信仰時,她思考了一下:「我沒有特定信仰,但一直都有戴著護身符,它現在也算我變裝國王的服裝之一吧,我想要表現出東方的元素。對我來說,我的Asian identity(東方認同)是很重要的。」
「身為一個東方人,可以玩的東西太多了」
台灣宮廟的平安符通常以紅色的薄塑膠做成小巧的方形,有人懸掛在車上祈求平安;或是像Echo一樣繫在脖子上,護符緊貼著心胸,求隨身保佑。
從風火輪到溜冰鞋,西方到東方,背後隱含的寓意一直在賦名之後才漸漸浮出;而Echo/Naza的自我認同似乎互為個體,又在無形中彼此牽繫。

Echo玩家已登入:乂走跳西方乂 三太子★Naza
圖片授權:@dragboinaza
對大多數的台灣人而言,護身符似乎只有庇護與認同的意義,但對於身在異地的變裝國王Echo來說,這個符碼還有與庇護同等重要的用途:展演。
「我的角色其實是比較intense(熱切、情感強烈)的,和亞洲宗教很合,身為一個東方人,可以玩的東西太多了。在荷蘭,這些元素可以讓我的變裝國王角色有獨特性。」她說。
Echo的變裝國王服裝,多是敞開胸膛、露出肉身的,小小的護身符成為服裝或飾品般的存在,隱隱標記所護之人的記憶與認同。Echo有意識地將它暴露在異文化的凝視下,從衣服布料下走出來的護身符與亞裔肉身,重整人們、包括Echo自己對於Asian和drag king的認知。
儘管自嘲著「本身沒有信仰,感覺有點像盜用宗教文化」,但Echo其實從許多面向去思考自己作為一介東方人,所帶來的展演意義:「我使用的物件,東方元素其實不大顯眼,但妝容的小細節曾經被說很亞洲,像是眼睛下面的痣、眉毛、鬍子,可能有幾分毛筆字的味道。」Echo自述,但自己也不會想做「百分之百」亞洲的角色。「我的角色設定比較像是,一個來到西方玩瘋的亞洲屁孩神(咦)」類似《聖☆哥傳》裡的耶穌和佛陀,在故事中過著日本人的生活。
「如果只是一味跟著『西方的』脈絡,我會有喪失自己的危險」
酷兒研究理論家茱蒂絲‧巴特勒(Judith Butler),曾引用傅柯理論提出自己的看法:她認為性別並非本質,也不只是一種「象徵性存在」,反而是一種社會實踐,他們抨擊性別差異的二元對立論,認為所有性別都是「表演」,是一種模仿,而性別角色只是「用來扮演、挪用、穿戴的世俗方法」,從某些角度而言,drag(變裝)文化確實是對抗二元型態最直接的實踐體現。[1]
與此同時,Echo也認為自己確實遇到了這樣的困境:變裝國王來自西方的文化脈絡,東方世界極少有前行者,因此難以演化出典範。而Echo要怎麼形塑自身的變裝元素,就是一個充滿挑戰性且有趣的問題。
與生俱來的東方身份對Echo而言有開創性的優勢,但相對也迎來了瓶頸。
Echo說起這份尷尬感:「在東方世界,比較少人在探索變裝國王的表演形式,所以如果我只是一味跟著『西方的』脈絡,我會有喪失自己的危險。」她舉例說明,變裝社群會參考的範本包含「西方」的古代服飾、「西方」的知名搖滾明星,藉此引起底下觀眾的共鳴──但這些元素,都與她所來自的島國台灣沒有任何關聯。
「換個角度來說,我希望有亞洲元素沒錯,但我又不要營造刻板的亞洲印象。」看似隨性發想的背後,其實是Echo對於自身定位的深刻覺察。「要玩刻板印象也是可以,我有想過要不要做一個K-POP表演,例如戴著耳麥跳舞唱歌之類的,但我目前還無法接受這個表演形式,可能之後再想想看吧。」她笑著說。
當然,這些反思與對談並不代表否定歐美脈絡底下的變裝文化。Echo在做的其實並不是強調 我/非我 的界線,而是希望:透過投入變裝國王的呈現,在清一色歐美文化的搖滾明星、男演員、古代人物典範裡,添加一些不同的元素,讓這個社群有更多樣性的面孔呈現。
摸索開創,實踐變裝
沒有適合的參考對象,不如就用自己的樣子去開創。
建構了內在自我以後,設計專長的Echo在視覺形象上也有靈活的運用。Naza的妝容強調眉毛,帶著幾分國王的氣勢與凌厲感。「我畫眉毛都是往上,然後眼下有兩個對稱的痣。滿常有人問我為什麼要這樣畫,其實是因為原本一邊就有痣,是我不喜歡自己的部分。所以我就想說,既然不能消除,就讓它對稱好了。我上妝時,都是找鼻子與眼睛的連線,讓痣和眉峰都落在有幾何構圖邏輯的位置上。」
Echo解釋化妝邏輯給我們聽,「原本我對痣有點自卑,但後來發現,對稱以後,整體的氣勢加強了很多。」我們深有同感。

Naza完妝後的正面照。
圖片授權:@dragboinaza
Echo也聊起化妝後逐漸觀察到的有趣心得,「我開始化妝之後,在電視上面看到一些女演員,我發現她們根本也在drag,畫得比我還多。」然而,普羅大眾對其接受度遠高於變裝表演者。
主流審美的眼光,為妝容的「自然/不自然」劃下危險的界線陷阱。「並不是每個人都在追求所謂的『自然』的美感。」Echo分享。變裝作為一種相對前衛的實踐行動,其實也是在拆解這種對於正常/異常的既定想像。

Naza Løtus, The House of Løst Bois, a work in progress, Amsterdam, 2019.
Credit – © Stacey Yates | www.staceyyates.com
濃妝上陣不只是一種形象操演,也是考量到觀者與表演環境。「House of Løstbois主要都在一間性俱樂部表演,那邊的環境很暗,如果妝不化濃一點,根本看不出來。」Echo說。
這間俱樂部有個諷刺意味極濃的名稱:「教會俱樂部」(club church),而且真有一個基督神像在吧台上面。實際登上舞台,又會面臨什麼樣的情境?
午夜揭開序幕,變裝表演者們輪番上陣。在這個小空間中,神性與慾望以一種奇異的方式遙遙呼應,一齣又一齣的戲碼才正要展開。

House of Løstbois 成員。攝於Club Church。
前排左至右:Lucian Squid, Rock De Bizzare, $NAKE
後方左至右:Naza Løtus, Silly Dick, Ariana
圖片授權:@houseoflostbois
[1] Robert Stam,《電影理論解讀》,陳儒修譯,遠流出版(台北市:2012)
濡沫 【泡仔聲】 ── 變裝國王Naza專訪
更多【泡仔聲】系列文字專訪,即將釋出……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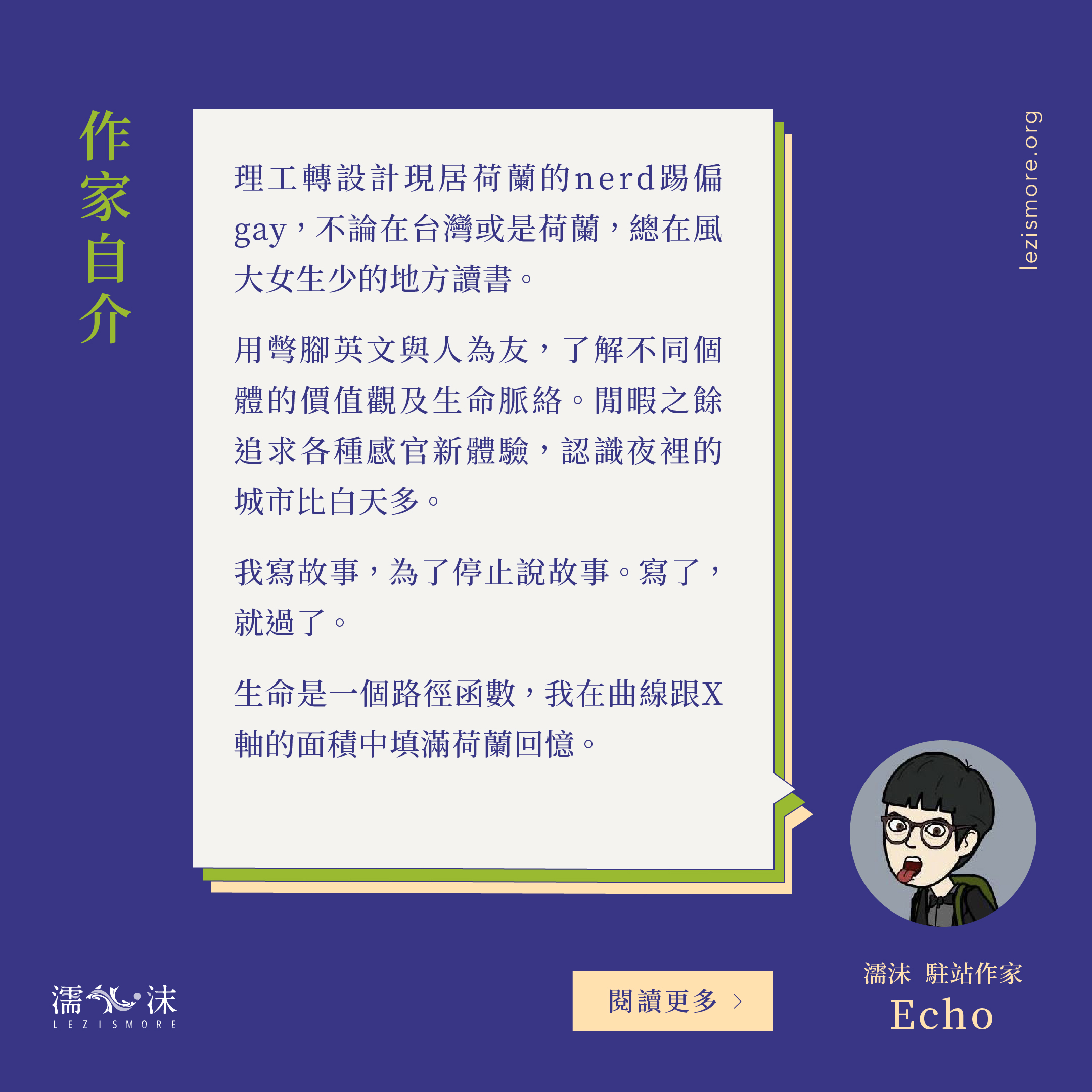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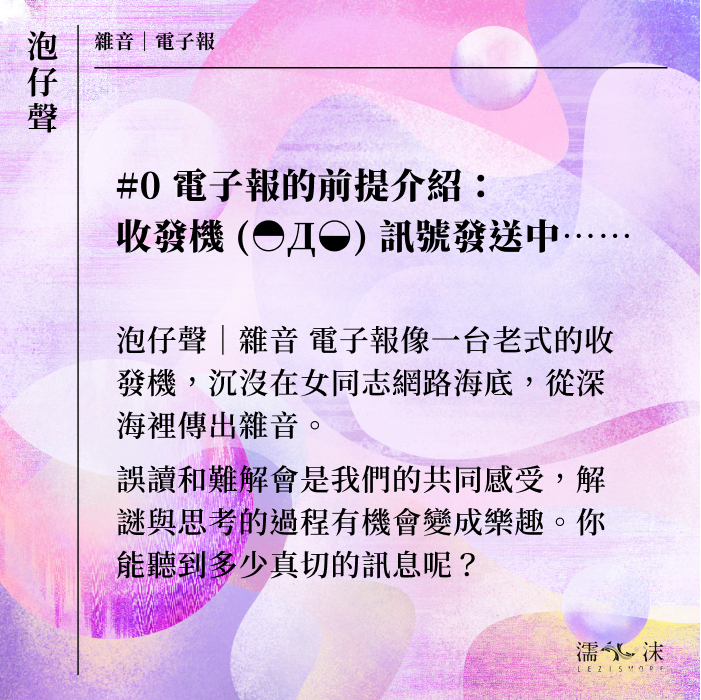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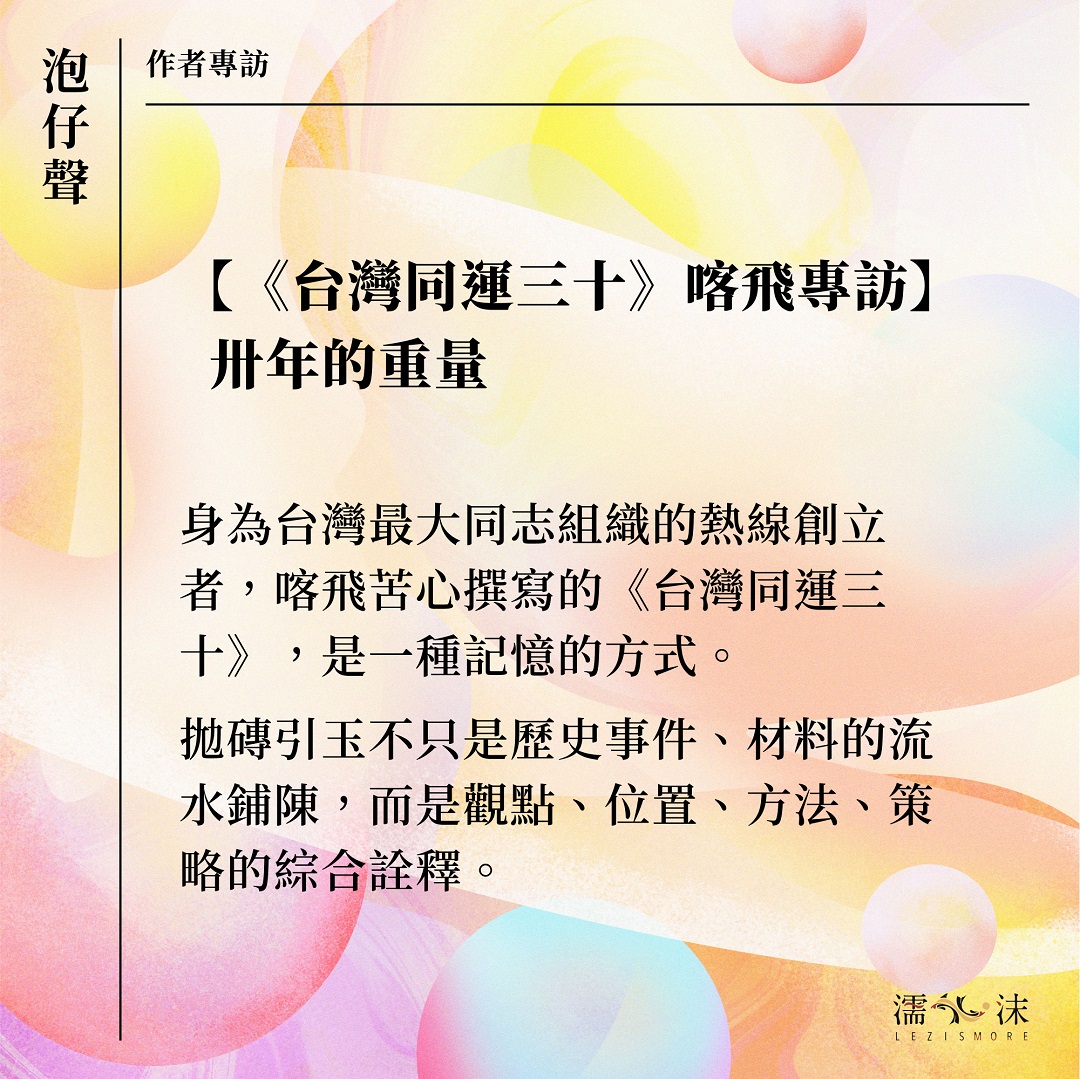

留言
You must be logged in to post a comment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