步入荷蘭卡雷國家歌劇院
在之前的專訪文章中,濡沫團隊與Echo聊到,她曾經以首位台裔變裝國王之姿登上荷蘭卡雷皇家劇院。接續前文提到的性俱樂部,Echo也分享這段登台表演的契機:「除了我們House of Løstbois,在同一個俱樂部還有另一個歷史悠久的元老團體叫作House of Hopelezz,他們的house mother其實就是俱樂部的擁有人,Jennifer Hopelezz。」
除了店內的固定表演,House of Hopelezz也是Superball 2019 [2] 的贏家,有不可小覷的前瞻性跟影響力。

The House of Hopelezz 團照。
前排金色捲髮的表演者為Jennifer Hopelezz。
圖片授權:The House of Hopelezz 粉專封面圖
在台灣提到變裝競賽,或許僅能聯想到Netflix上炫麗的魯保羅秀(RuPaul’s Drag Race,美國真人實境秀比賽的電視劇)。但是House of Hopelezz的亮點並不算是以氣派華麗的風格勝出。
「其實他們衣服預算不是最高的,也不是最『美』的吧,成員組成很不同。例如有一些比較大尺寸的queen啊,也有不同族群走秀,他們的突出之處就是多元,各種性別、年齡、族裔都有。」 Echo解說。
Superball 2019 的年度變裝主題是「革命」(REVOLUTION),當多元作為革命的手段,似乎也昭示了我們對於性別界線還有更多值得玩味、打破、重建的可能性。
「我們的mother,TAKA TAKA,是House of Hopelezz的成員,得獎後,Hopelezz有很多表演邀約,其中包括荷蘭歌手Wende Snijders的卡巴萊(Cabaret)演唱會,這個在荷蘭卡雷國家歌劇院的機會是大亮點之一。出於母愛(?),TAKA TAKA把House of Løstbois也列進表演名單,這應該是我們第一次去那麼隆重的地方表演。」Echo說。
不走誇大厭男路線,探索屬於自己的展演
Echo的舞台探索,實際上並不亞於實踐變裝的複雜性,在大舞台上的展演只是揭幕。
「我對變裝沒有太大的困擾,但我對『表演』其實有很難跨越的坎。」Echo與我們分享,因為自己既不是表演背景,甚至有舞台恐懼(stage fright)而排斥上台表演,所以一開始的表演都會喝醉。
「我都即興表演,沒有辦法像別人一樣可以做完整的表演計畫。」Echo甚至不諱言,自己不喜歡變裝國王的傳統形式。傳統的變裝國王,很多時候是在展演一種有害的男子氣概(Toxic masculinity),表演者去展現出「男子氣概」的形象,比方說做一些很糟糕的男性行為,然後誇大及強化它,時常用以諷刺或帶來娛樂效果。
Echo不以為意地聳聳肩:「這樣比較沒新意。再來是,形式上也是我不擅長也不會想要做的事,例如說對嘴唱歌(lip syncing),或是塞假陽具來諷刺陽具的不方便性,去激起類似『men are useless』這種厭男情緒。」
於是Echo的舞台表演常常是舞蹈,一方面是因為符合自己的人設,二來也是喜歡跳舞。
「我喜歡上台跳舞,但對我來說目前跳舞要當成正式表演很難,因為它沒有劇情。但表演構成的基本就是要有轉折,還有結尾的驚喜感。」Echo認為,比較非主流的表演可能才是自己愛好的類型,也是未來Naza可能會經營的路線。
Xenia的表演:我不需要服裝,我的身體就是我的服裝。
訪談中Echo特別提到House of Hopelezz裡面的一位舞踏表演者Xenia,並且詳細介紹當天他在的表演細節:
「Xenia不是drag king,生理女性。對我來說,他是性別流動的極致,他把身體練的同時具備男體跟女體的魅力,不太依賴化妝,抹上舞踏舞者的白,純粹得有如希臘神像一般。」
「當天他在皇家劇院的solo非常大膽。舞踏表演者的白身,戴著長假髮、上空,並只穿著藍球褲跟塑膠拖鞋,搭配著歌劇,跟莊重的超大場地映襯起來,充滿衝突感,也顯示他作為表演者的膽量跟氣場。」

表演者 Xenia Perek(photo by Roberto Apa)
「表演的內容是這樣的:他一邊對嘴,一邊戲謔地把兩隻拖鞋踢遠。接著,他開始把籃球褲的鬆緊帶拉開,歇斯底里地向球褲內看,接著他以吊人胃口的方式,慢慢脫掉籃球褲,然後踢飛。」
「最後,他全身僅剩的布料只有一條白色的Jock strap。然後,他在褲檔裡掏出了兩條白長襪,慢慢地,用耐人尋味的方式把長襪一條一條穿上,結束他的表演。」聽起來簡單,但各種衝突的元素,加上他的個人表演張力,就形成了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表演。

表演者 Xenia Perek(photo by Raymond Van Mil)
「他的這場表演,其實讓我可以連結到House of Løstbois上過的一個脫衣舞工作營的內容,使用了許多營造預期(expectation)的技巧。在Xenia給我們的身體工作營中,他也說過一句讓我印象深刻的話,他說:『我不需要服裝,我的身體就是我的服裝。』這句話讓我不禁思考,我跟我的身體之間的關係能否再更親密?我能否用非二元的眼光來看待自己的身體?……」Echo陷入了長長的沉思。
Uber拒載?我們自己扛轎!──國王們的正式「出道」
表演的本質,是一個動態的演變過程;表演者、表演場域、觀眾組成,都會影響到實際演出的情形。例如在夜店這種昏暗與喧囂並存的場合,其實就很難做太有深度或是過於靜態的表演:「或是說你真的要夠厲害,才能抓得住人們的注意力。」Echo說。
Echo/Naza的正式「出道」,被更多人看見,是源自2019年初的Drag Olympics。這是一場人數約兩千人的戶外定點活動跟party,每年會固定在荷蘭的同志紀念碑廣場舉辦。

遊行當天Jennifer Hopelezz乘坐於改裝計程車,前排配戴黑色帽子的表(抬)演(轎)者為Echo/Naza。
表演者由左至右為:That Guy Rafaël, Lucian Squid, Naza Løtus, Rock De Bizzare, $NAKE
圖片授權:@dragboinaza
Echo說,這張照片是活動開始之前拍的:「在車子上面那個人是Jennifer Hopelezz。在活動前他和uber還有市政府簽了一個案子,內容是:計程車不能拒載任何種族、膚色,或是性別取向的人,當然包含drag queen。」
「簽約完不久,他們(變裝表演者)打算搭Uber過去拍宣導影片。諷刺的是,那個Uber司機竟然惡意拒載,說他屁股太大了坐不下。」Echo繼續說,「這件事發生的同個時期,我們剛好在討論轎子的形式,因為每年的遊行活動他都是像媽祖一樣被抬出場。受到Uber事件的啟發,我們買了一個車子造型的兒童床,把床改造成計程車造型的轎子,算有意識地透過這種展演去回擊吧。」

Echo的變裝照片,攝於荷蘭同志紀念碑廣場。
圖片授權:@dragboinaza
除了「街頭出道」的抗爭色彩,活動當天也有許多輕鬆有趣的過程。
Echo回憶:「那天我們有走秀(run way),一直在台上跳舞,維持台上的熱鬧度。這好像是我們第一次去女生比較多的活動,畢竟我們之前都是在男性為主的club裡面表演,所以那天超多女生尖叫,我們還滿飄飄然的。」
相對drag queen而言,king其實是非常少數的族群。在活動當天,House of Løstbois因此受到了很多關注。「那天超high,然後一直有媒體來採訪跟拍照。」Echo笑著說。
社群初起步,長路仍漫漫
因為有了公開活動的曝光,House of Løstbois的成員開始被訪問,或是登上酷兒的小眾媒體。
「因為我們的社群其實是比較政治性的,一般drag king的house,比較少有這種類型的元素。」Echo所隸屬的變裝家族,有相對緊密的社群關係,也有固定的空間與表演機會。
問及Echo是否認識drag king的散戶表演者?他們可能會面臨什麼狀況?
「他們可能會到處去不同的城市或節目,也許某一集節目會特別在找drag king主題,就會連帶認識其他drag king,但一起表演的機會比較少。」Echo向我們分享身邊所見所聞的案例,如House of Løstbois裡有一個成員,自己也有另外在家鄉建立當地drag社群。
「但就要非常積極的組織網絡,做社群行銷啦,去和其他變裝皇后打好關係等等,才會有比較多機會被邀請去表演亮相。」即使drag king的酷兒族群較少,但仍然有其不同的路線選擇與發展方向。
一如所有文化,變裝文化也有自身的脈絡與演進史:即使drag king與drag queen在同一個場域裡有交流、競演、互助的可能性,仍有各自的展演策略與多元眾生相,實踐者對於「表演」的呈現自然會有許多不同的想像——對照現行社會中為了拍「宣傳片」而被拒載的變裝皇后,以及遊行當天也有另外兩個變裝國王被拒載的案例。即使是在相對性別友善的荷蘭社會,仍然也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。
而這裡所發生(過)的一切,都還不是尾聲。
[2] 歐洲境內規模最大的變裝競賽(drag competition),得獎名單網站可見:https://www.paradiso.nl/en/program/superball-2019/54780/
濡沫 【泡仔聲】 ── 變裝國王Naza專訪
更多【泡仔聲】系列文字專訪,即將釋出……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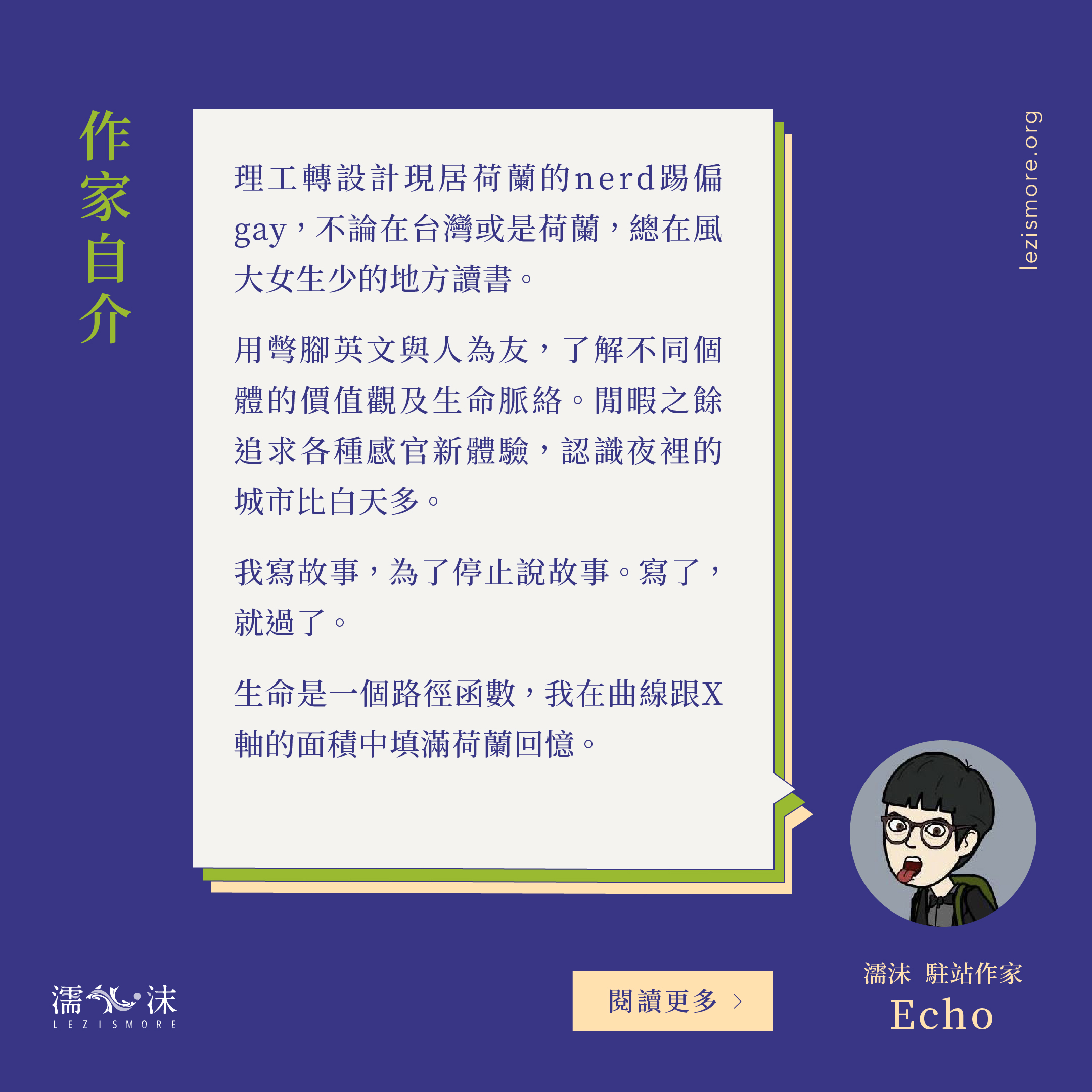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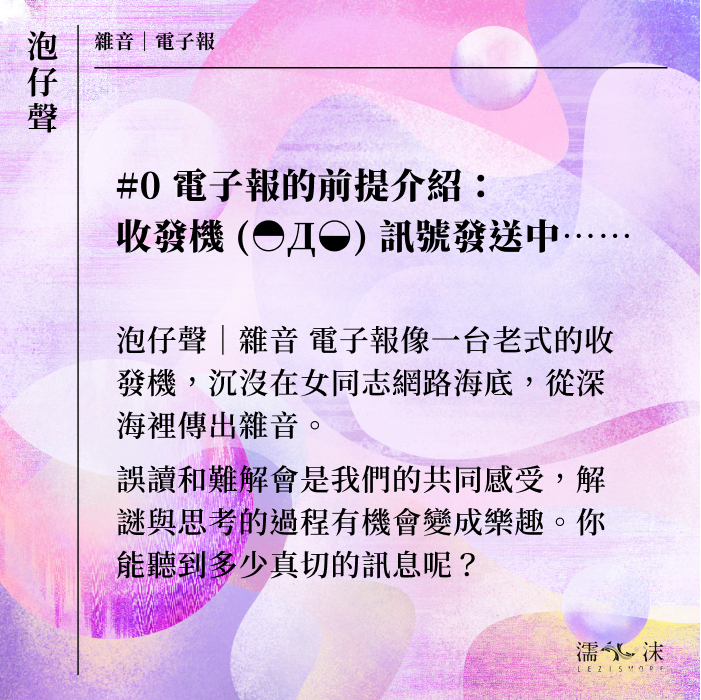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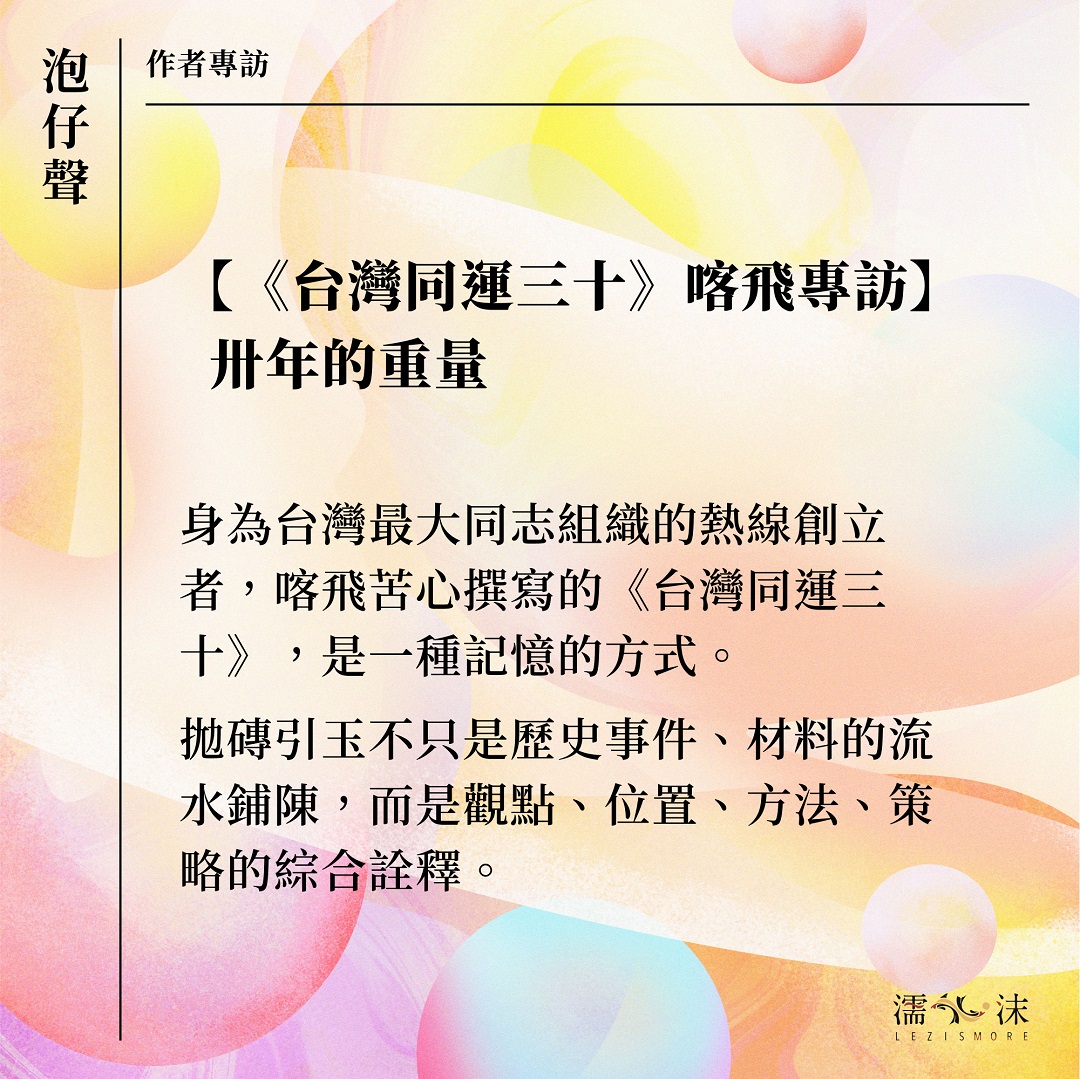

留言
You must be logged in to post a comment.